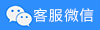富山平車,自動倒回針,回不了原位,應該怎么調?
,兩個辦法解決,一個吧倒針后退的針數調多點,一個打開后蓋把倒針針碼調的跟前進針碼一致,倒順縫不一致,顯示屏上的數字全部2222
周期往復,尋找穿越
俄烏局勢則可能是另外一個更長期的變量,它后續的“余震”還在醞釀之中,暫時既無法評估也無人知曉。唯有能夠確定的,就是即將到來的全球供應鏈不確定性和全球經濟下行壓力。
這些都讓一直波動不休的經濟周期,更加撲朔迷離。與此同時,一種以技術變革所帶動的產業周期,也在開始出現新的浪頭。一如特斯拉、蔚小理等電動車帶來的造車新勢力,或者是雙碳目標所帶來的綠色能源,或者是數字化轉型帶來的數據淘金,都需要久經沙場的老將們,抖擻精神進行應對。激烈廝殺的戰場上,出現了陌生的面孔。
經濟周期充滿了波動性,而產業周期則充滿了破壞性。雙重疊加的周期,讓中國企業家所要邁步向前的路,到處插滿了不確定性的小旗子。
在這些信心難免動搖的動蕩之下,增量收入成為艱難時局的亮點。但仍有一些中國制造企業交出了不錯的答卷。2021年,京東方、比亞迪和TCL收入都是大幅度增長,闖入2000億元俱樂部。美的集團在三個季度收入超過2600億,年度將輕松破關3000億。濰柴集團也繼續保持增長,銷售額在5000億元以上,并且將2030年目標定為萬億。聯想集團最新數據顯示,整個財年的營收有望超過4500億人民幣,相比兩年前的3531億增加了27%。而在最新的財年誓師大會上,“架設云梯、穿越周期”也被明確提出。這些增量收入俱樂部,在后疫情時代的迷霧之下,是否準備好了再次穿越周期:在“擴張、觸頂、下滑、觸底”的周期中,完成螺旋式的上升。
全球化:均衡器
正在進行的俄烏沖突,或許開啟了一個危險的極限外交時代。除了斷交,其他措施都是無所不用其極。而外交手段可能斡旋的空間,被壓縮得像保鮮膜一樣稀薄。我們更是看到,歐美與俄羅斯的供應鏈之間進行了一種撕裂式的硬分離,凸顯了全球化的危險性。
全球制造的風險以各種等級進行釋放,除了極端情形,更常見的則是通過壓縮供應鏈的流動性,在更小的區域流動,形成區域性制造,這兩年尤其常見。美國、日本、歐盟等發達工業國家都在強調如何把供應鏈搬到本國,強化本地制造。與此同時還加大制裁和限制措施,給后面的追趕者施放更多冷箭。而相對價值鏈較低的東南亞國家,也在試圖從原材料開始進行更多的裝配制造和深度加工,拓展本地全面工業化的步伐。實際上,他們正是希望從中國占據優勢的制造業領域,分得一杯羹。
不可否認,東南亞國家這幾年在制造快速崛起,形成不可忽視的制造新勢力。越南自不必說,跟墨西哥一樣,作為兩個最大經濟體的鄰居,充分享受著美中貿易戰之下的當地制造紅利。而原材料資源豐富的印尼,也在考慮如何把鍋蓋子按得再緊一些,肉和湯都要留在鍋里。印尼是全球最大的棕櫚油出口國,也是鋰電池發展所必不可少的優質鎳土礦的大戶。印尼政府,正在考慮所有的原材料都不出口——所有的大宗商品。如果其他國家想利用這些資源加工,那就必須到印尼來投資,在本地設廠。韓國LG集團則簽訂了一份上百億美元的電池投資協議,其中規定用于鎳礦中至少有70%必須在印尼進行加工。印尼既有的工業基礎設施能否消化這些原材料,是一個問號。
俄烏沖突之后,一些公司如3D設計軟件美國歐特克,迅速采用了直接跟俄羅斯切斷關系的硬切割方式,就像是將輸液管突然拔離。但俄羅斯對于歐特克而言,并非關鍵市場。這種魯莽的“拔管”動作,與其說是見證了兇險,不如說讓人意識到二者之間的浮草而脆弱的依賴。而中國制造,需要反其道而行之,在全球建立廣泛的盤根錯節的制造基地,使得相互顧忌。胸有大海破浪,更知江湖行舟。企業家需要在全球格局下,下出一盤大棋。
一些卓有見識的企業家,已經看到這一點。TCL旗下的華星光電這兩天宣布,印度華星生產的面板,已經通過認證開始正式供貨三星。而未來,將大力推進在印度的生產本土化,扶植印度本土供應鏈。這一行動,被一些人反擊認為不能壯大印度工業。殊不知,全球化的供應鏈是互相粘連,三星、LG已經退出液晶面板,它們依賴于中國華星和京東方。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泥水關系,會形成對中國制造最有利的根系相連而固化聯系的作用。將來誰想擺脫誰,都不容易。3月底美國通過的芯片振興法案,要提供450億美元圍繞美國、日本、韓國等建立Chip4芯片聯盟,就是要封堵中國。而韓國,則警惕地表現出淡漠。
這就是全球化的均衡器效應。
戰火四處點燃,到處都有角斗。在印度尼西亞這個全球第四人口大國,日系車占比超過95%。而上汽通用五菱則通過在印尼建立制造工廠,正面向日系車發起挑戰。五菱的本土化制造,也是一種“扎硬寨、打呆仗”的做法,帶領中國的供應商在日本鈴木印尼工廠的對面,建立汽車園區,同時開設了128家經銷門店。而在印尼電動車的標準體系上,印尼政府正在邀請五菱為主,參與電動車的標準制定。這是日本車系的禁臠,多少年來這些權力都把控在日本勢力范圍內。而現在,捅破天的機會來了。這些努力,得到了印尼總統和內閣官員一致的好評,他們紛紛到上通五菱的展臺去拍照,這些部長們也四處為五菱代言。
本土制造,是最好的外交。
而在過去的一年,上汽通用五菱,已經在印尼取得了3%的市場占有率,這都是虎口拔牙的戰績。這是中國在全球化的市場中,通過彪悍的韌勁,撕咬出來的。而作為很早參與全球供應鏈的公司,聯想集團七成營收是在海外獲取,而生產制造則90%都扎根在中國。
當前的全球化,已經是大國較量加上小國博弈所撼動的地殼運動。全球化的思路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在中國加入WTO進入成熟期;而在金融危機之后,又在緩慢走向新的形態。全球供應鏈大的嬗變,已經開啟。有志于穿越周期的企業家,應該來到炮聲最密集的陣地。越是寒流洶涌,越要堅定信心走全球化道路。全球化是抵御國際化寒流的唯一法門。
供應鏈共同體:穩定器
中國制造體量巨大,占全球制造業增加值的30%左右,這給中國制造的韌性,給力圖穿越周期的企業家帶來了一個周密的保護傘。龐大而周全的制造體系,使得中國制造供應鏈并非是一個鏈條,而是呈現輻射形的網狀分布。上下游線性關系,已經被復雜的網狀連接所取代。活躍的產業生態網絡,呈現出一種類似生命體的有機結構。
正是這種生生不息、互聯關聯、利益共生,產生了穩定器的作用。
當下,中國已經超越了“超級工廠”,成為全球供應鏈網絡的“超級節點”。但是,這些沒有感知的供應“鏈”,它們在哪里?
答案是,它們就像海底深網,早已在海底撐開。很深,但不可見。只有借助龍頭的視角,才能找見它們。
龍頭企業,讓這些交織融合的有機體,清晰可見。麥肯錫發布的一個報告,將主流電腦供應商的供應鏈進行了對比,發現聯想集團供應鏈的聯系層次要比戴爾的深很多。戴爾用得更多都是自己的生力軍,獨有的供應商;而前者則更多地采用共性企業,帶動了6000多家公司參與了共創。它在合肥的制造基地聯寶科技,自安徽工廠落地以來,吸引70余家上下游合作伙伴落戶于此。這對于生態的維護,有著巨大的促進作用。一個驚人的生態群落,在這個網絡節點上進進出出。
圖 戴爾和聯想的供應鏈比較(來源:麥肯錫)
這樣的供應鏈生態,意味著什么?一臺電腦和它的供應鏈,有什么意義?
讓我們重新思考一下全球分工的含義。斯密亞當的比較優勢和專業分工論,可以簡單看成是分工是基礎,交易是目的,而資本家則是通過交易獲益。積累社會財富的多少,讓位于資本增值的多少。而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很早就主張“實業興國”,他認為以交易為基礎的工業發展道路,是忽略了“生產力”的根本作用。“財富的生產力比之財富本身,不曉得要重要多少倍。”德國人一直篤信李斯特的理論,百余年不變。“生產能力,不僅是已有的獲得保障,而且是已經消失的獲得補償”,李斯特的聲音回響到如今。因此,可以看到德國制造業的GDP占比多年一直在20%左右,這在發達國家是非常突出的比例。
不妨說,一個國家的生產能力,比產品本身更重要。電腦制造能力,比電腦本身更重要。
即將到來的車載計算、混合云、智慧城市、智能服務,或者中國剛剛宣布的“東數西算”計劃,背后都是計算的支撐,而這些都是離不開這種制造能力的保障。
這種能力是靠著體系的保障。企業之穩,穩在中國根基,穩在自有制造。在全球三大電腦制造商,惠普和戴爾都是貼牌生產,而聯想集團是唯一堅持擁有自主工廠基地的廠商,且絕大部分都在中國本土制造。它在安徽合肥的聯寶工廠,每1秒鐘,就會下線一臺電腦。而全球每八臺電腦,就有一臺來自合肥。這讓其成為合肥市第一家超過1000億產值的企業。同樣,它在武漢工廠所生產的手機和平板電腦,成為這個城市最大的出口創匯源泉,單廠出口產值相當于武漢1/4和湖北省的1/8。聯想集團之于武漢,就像富士康之于鄭州,一個制造大廠撐起了一個城市乃至一個省份的外貿出口。立足于本土根基,但觸角遍布全球。
這些代表著中國蕓蕓眾生民生大計的數字,既無法體現在財報收入之上,也無法體現在它的產品形態之中。區域經濟與龍頭企業,相得益彰。只有下潛到民生視角,才會理解一個龍頭企業的制造能力的含義。也正是這些供應鏈的深海網絡,和那些深不可見的連接,讓這些龍頭企業,不僅僅自己穿越周期,也帶動上游大小企業,一起涌動向前。
供應鏈的韌性,是穿越周期的穩定器。無數這樣的供應鏈深網,也成為一個國家抵御風浪的沉錨,讓基盤保持穩定。
數字化:加速器
從產業發展周期來看,一個行業會不斷地新陳代謝以維持生命體,不會斷然消失。就像是老樹發新芽一樣,不斷在母體上長出新的生命。即使新興產業,也并非從空而降。紡織是不是傳統制造行業?而美國先進制造正在考慮把電子、芯片做到衣服里。這意味著,一件電子服裝既能發電又能通訊還能計算,已經成為地地道道的數字化中心。而摩托羅拉正在美國開發的5G項鏈,數字化附身,一件普通的珠寶擁有了神奇的通訊力量。而全球動力電池大王寧德時代,在去年年底也注冊32億元成立了工業軟件公司。這背后的邏輯是,汽車的價值正在大踏步地從鋼鐵轉向電子與軟件,一輛特斯拉汽車的代碼數量超過2億行。這不由讓人想起最早在中國進行數字化普及的麻省理工實驗室的尼葛洛龐帝教授所帶來的《數字化生存》一書,還有他一直口中念念有詞的“Move bits, not atoms”(多移動比特,少搬移原子)。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而現在,比特與原子,終于更加緊密地糾纏在一起了,沒了邊界。
一個企業的邊界在哪里?對于一個企業家而言,這是高質量發展所繞不開的命題。而數字化轉型,則給出了一個一箭雙雕的答案:它既為自己深耕土地好打糧食,也突破既有邊界發現新疆土。
聯想集團正在將一種數據即服務DaaS的服務,提升為全棧式的數字化辦公空間解決方案,從而為疫情之后迅速崛起的居家辦公和工廠遠程運維提供全新的服務模式。這種思路首先來源于疫情期間應對武漢封城的對策。在2020年二月份疫情還是未知的洪水猛獸之際,借助于扎實的數字基礎設施,快速復工。“4月實現100%滿產”,這是當時《彭博商業周刊》英文版五月刊的封面報道,以這個故事來講述“武漢重生”。重生是需要全新筋骨的,這種筋骨支撐了新制造體系的運轉。很快,它也變成了其他企業樂見、樂用的解決方案,進而變成了可對外實施的服務。
這是一個邊界重構的實踐,聯想集團將其定義為“內生外化”。簡單說就是自留地里種出來的菜,我可以吃你也可以吃。“內生”是利用自研的產品去推動公司的戰略轉型;而“外化”則是將內生過程中經驗證的解決方案推向市場,帶給相似需求的客戶。自己先用,豁然開朗;對外賦能,日朗景明。
當下很多制造大廠,為了提高自身的智能制造水平,都采用了數字化轉型方案,而大量都是可以對外復制的,變成一種企業對外服務的方案。源于自家工廠的視覺檢測方案,TCL旗下的數字化公司格創東智,正在為很多3C工廠實現自動化的質量圖像檢測,從而代替檢驗員靠眼睛確定缺陷的繁重崗位。同樣,這種衣服里子外穿的嘗試,也讓聯想集團本來為自己開發的混合云解決方案,為基礎設施即服務IaaS,帶來了更多的額外價值。意味深長的是,它將潛在市場的容量,一下子從20億美元擴展到了300億美元。
邊界被打開了。數字化,就像是一個開瓶器,它釋放了一種被鎖住了的力量。依靠全新的IT理念,重新形成數字化技術技能,這是穿越周期的關鍵一步。
聯想集團的企業文化里有一種“復盤文化”,偏重總結。復盤,經常是一種經驗性、松散性的回顧與總結。現在,它的質量部門,將這種復盤文化,帶入到一套數字化流程體系之中。這讓質量的追溯,有了一個可支撐的把手,就像登山路一側的欄桿,抬手可見。這種量化有序的質量管理軟件平臺,既可以帶動企業質量發展,也可以帶到供應商質量的體系之中。
先實踐,然后IT固化而“內生”,一個制造企業不斷優化的流程會打造更多的合手的工具。這意味著,“內生外化”會有著源源不斷的新武器。數字化成為一種加速器,快速穿過邊界模糊的地帶,找到全新的利潤點。
只有重新定義邊界,才能找到更大的藍海。美的集團,除了在既有的家電領域之外,也開啟了全新的邊界:美的工業。2021年是美的機電事業群發展的一個新起點,面向家電、汽車、工控、3C的工業解決方案已經全面展開。
實際上,美的在工業領域的探索,由來已久。在全球每2臺空調中,就有1臺是美的工業旗下的美芝壓縮機。而它收購以色列的高創伺服控制器、合康高低壓變頻器,已經讓它在自動化領域悄然合圍,而在2017年收購的德國機器人庫卡,則是這其中最驚艷的手筆。這一國際化并購,它給德國人的驚愕徹底改變了德國精英層對于中國制造的認知。毫無疑問,傳統的家電行業的邊界,已經被打破,新產業的疆土正在腳下延伸。這些基于電機、電控和精密機械等領域,正在為美的穿越全新的周期,布局了幾條支撐腿。有了跨前一步的腿腳,自然就能丈量出無盡的邊疆。美的工業的這些方案,還在合攏之中。但它們必然會在數字化驅動之下,向著一個業務邏輯統一的中心球靠攏:統一成更加強有力的美的數字工業事業部。美的將壓縮機、變頻器、控制器等自己所用的業務,從自己使用的“內向”到推向外部工廠的“外向”,正是一種典型的“內生外化”。
內生外化,就像是一個兩棲動物一樣,是脊椎動物進化史上的一個奇跡。作為水生到陸生的一次高級進化,這是脊椎動物走向大陸、走向新周期的一個里程碑的穿越。而數字化,則是一個超級系統在自然進化中的基因突變量。